按语
本学期,20级本科新闻和19级本科播音班分别开设《新闻采访和写作》和《新闻采访》必修课,2021年9月开始由陈红梅老师主讲。国庆节后,同学们进行新闻采写综合练习,陆续提交课程作业。经补充采访修改完善后,任课老师将挑选一部分优秀作业,不定期刊发。
“逸夫楼前那个邮筒我不喜欢,像块墓碑。”
开箱班邮递员王霞一边乐呵地开着玩笑,一边蹲下身去开信箱,“原来还是高高的,后来这栋楼改造了,邮筒的底座就被埋进土里了。”
距离下一个邮筒开筒时间还有四五分钟,秉持着“不能早开”的工作铁律,王霞放慢了车速,在必威东盟体育平台中北校区内慢慢转悠起来。她左脚踩在踏板上,右脚往后弯踩在后轮旁的铁架上,左手胳膊肘上还挂着一条长绳的绿色卡套。“不用校园卡,我刷身份证就能进华师大学校。”王霞一边骑车一边笑,“华师大以前是我玩的地方,那个时候和同学们每人从家里拿个菜就在白石桥上吃。”
“还有一分钟。”王霞加速了。

逸夫楼前的邮筒
她穿得比常人更厚一些
12月17日13时54分,王霞出现在了华师大邮政所门前的第16号邮筒前。寒潮到来的第一天,王霞穿的比路人还要厚重些:一件加绒保暖内衣,一件遮住了嘴和下巴的半高领羊绒衫,只有透明护目镜后的眼睛露在外面。她在自己的棉袄外还穿了一件印有“中国邮政”的靛青色防风衣,一块黑色加厚的防寒护腿神器紧紧包裹着她的小腿和膝盖。“我们这个行业,最遭罪的就是天冷。我记得上海最冷的时候零下七度,一直吹风。”王霞说道。
从车头前贴有红蓝条纹装饰的快递信封专用箱中取出钥匙串,只看了一眼她就已经把16号邮筒的钥匙捏在指间了。钥匙串上有21把贴着红蓝两色圆珠笔字迹的钥匙,上面是王霞写下的各个邮筒的代号,如“788”“怒中”“长所”,都被透明胶密封着以防雨水打湿脱落。几乎所有的绿色邮筒下有个三层石基,王霞的个子差不多只到投信口处。弯腰、开锁、取信、上锁,一整套动作只用了不到20秒的时间。大致看了下手中信的收信地址,王霞就把它们都塞进快递信封专用箱里的绿色邮差包,启程前往下一个邮筒。
刚出发几米,邮政所里的一个员工把她喊住了。王霞停下车,身体往前倾了约45度,才让两只脚勉强都踩在地上。匆匆几句话后,王霞骑着电动车汇入了马路上的车流。
“1小时25分钟。”开23个邮筒一共所需的时间,王霞脱口而出。14时35分,王霞回到曹杨新村邮政支局,她把车停在门口,拿起邮包就进了邮局。王霞的邮政电动车是“改装”过的:一块黄色雨披包裹着车灯和电机,她说怕下雨潮湿有危险,就自己动手剪了雨披布包着;黑色的加绒手把套藏住了车把手;还有一件浅青色的羽绒衣被王霞用回形针和皮筋搭成的大皮筋绑着,刚才她在骑车时是敞开挡风的。
一进办公室,油墨的味道扑面而来。这间办公室的面积约有10平米,两张摆满邮资机、打印机、电脑的桌子就占据了一半的空间。电脑上只开着邮政系统的网页,一台空气净化器嗡嗡地响着,因为这间办公室里还有一个散着味的窨井盖。

王霞办公室的一角
把信件取出,把邮包放在桌下的塑料筐里,王霞拿起桌上墨盒里的邮戳就开始给信件盖戳。“啪”,“啪”,有点分量的邮戳砸在信上,正好盖在两枚邮票间,留下一个一元硬币大小的油印。“盖了邮戳的邮票就不能再用了。”王霞解释道。
接着王霞把这些信件都扎进了一个布袋,交给了其他部门。测试邮资机的使用状况,逐个扫描一张贴满邮筒二维码的表,在工作簿上盖上今日的邮戳与自己的姓名章作为每日打卡,王霞忙到了17时14分,距离下班还有16分钟。身旁的女同事外放着声音在浏览抖音,王霞也玩起了手机。17时30分,王霞定的闹钟一响起,她就立马站起身,逐个关闭电脑、打印机、邮资机、空气净化器的电源,收拾了一下桌面。
王霞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马上二十年了”
再过一年,王霞就在这个行业干了二十年整了。
“其实我最开始是想做老师的,华师大可是我以前经常玩的地方”,夕阳的余光反射在王霞的眼镜镜片上,像是从王霞眼睛里放出的光,“我希望孩子们遇到一个好老师,不要像我一样被一个不太好的老师留下阴影。”王霞回忆起她小学时候,因为追求漂亮,就披着丝巾在村里溜达,结果被同村的一个老师告状给了班主任。上课的时候,班主任把一串珠子挂在她头上,嘲笑说“你不是爱美吗,让你美”,这次经历给王霞留下了阴影。但最后因为成绩等限制,她的老师梦画上了句号。
旅游技校毕业后,王霞做过很多份工作。先是旅游服务业,再是音响和童车生产车间的女工,因为觉得流水线工作太死板后王霞又去了江南造纸厂,从事邮票的造纸工作。刚入职不久,下岗潮就来了,江南造纸厂因为污染等问题要搬迁,王霞听到解聘新员工的风声后决定主动辞职,对方也没挽留。后来王霞去做了买传真机的销售。底薪2000元,卖掉一台再奖励50元。待了三个月后王霞又放弃了这份工作,她说她不喜欢闷在办公室里,也不怎么愿意把成本较低的传真机高价卖给客户。后来她也考虑过保险甚至传销工作,身边的人都劝她“进邮局吧,别折腾了”,王霞也觉得年纪有点大了,得安定下来了。
除了工资较以前低了1000元左右,邮局的工作对王霞来说其实是份挺好的工作:没有人对她的工作指手画脚,不用天天对着电脑,她可以在外面自由自在地运动,还有一点——邮局不会裁员。2002年,王霞进了邮局,成为了一名邮递员,一做就是十九年。
“我刚进邮局的时候我姐就说你能干啥。我一听不乐意了,别的女人能干我就不能做啦?”当时的邮政专用自行车车轮是28寸,比现在生活中常见的24寸的哈啰单车高出了约10厘米,而王霞的身高只有1米56。 “那个坐垫到我这儿,”王霞挥着手臂比划她的腰,“我爸帮我用铁锯把坐垫下的铁杆锯了我才能够到。但就算这样,我干活时还得跳上跳下。以前车上还要装五十斤的东西,刹车时你得用脚使劲撑着才不会摔下来。”停车送报时要把整辆车抬起来才能放下后轮刹车的方蹬,而两幢居民楼间隔了十米,这意味着王霞每隔十米就需停车投递,每隔十米就要把车抬起放下刹车方蹬。“一开始抬不起来,练到后来都有肌肉了。”王霞一边笑一边捏了捏自己的肱二头肌。“后来考虑到量大活重,邮局出于体力的考虑少招女的了。”
投递员的工作不只是投递,首先要把每封信所处的门牌按规定路线的顺序排好,最多的时候一趟要送七样东西:报纸,挂号信,平信,账单,快寄,小包和从国外寄来的包裹。所有的东西都按顺序排好后,理顺投递的顺序,不然就需要送完一样再掉头返回。“我们干到最后都闭着眼送了。”王霞做了十六年的投递员,三年前才转到了开箱班——主要负责开邮筒,她直言是因为太辛苦了。“外人看着简单,以为是按门牌号1号2号这样有顺序送的,其实不是,不少小区的门牌既有老号又有新号。”王霞举了个例子,有的老房子原先的门牌是三十几号,但翻新后门牌就变成了一百多号。如果不记住,所需的时间就会延长。说到这儿,王霞回想起自己刚开始工作时每天做到晚上八点半,在雪夜一边哭一边骑着自行车送报的场景,笑了起来。
“最辉煌的时候过去了”
这么多年,王霞每天都要走过枣阳路、金沙江路、中山北路,从曹杨一村二村到华师大二村三村,地界上2000多户人家,她说自己比居委会还要熟悉。“我坐不住,喜欢每天在外面溜达,做邮递员有时候空了还可以跟这个阿姨那个阿姨聊聊天,挺好的。”
当问到以前工作的光景时,王霞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声音也随之变得激动。
“以前大家都写信啊。我年轻时就写过很多很多信,男朋友当兵的四年里我们就写信,信厚到像一本字典那样。本来想要装订成一本书的,但1990年代就已经要800块了,就算了。”哪怕两人最后没有走在一起,那段依靠书信寄托感情的经历也让王霞铭记,投递书信也成为她后来到邮局的部分原因。
走过必威东盟体育平台的樱桃桥时,王霞把原本挂在左手手肘的外套转移到了右臂,右手上还抓着口罩的带子,特地腾出左手指向河对岸说除了秋林阁门口,逸夫楼前还有个邮筒。十几年前华师大校内邮筒的盛况,是王霞关于华师大最深刻的记忆。“以前这个时候,华师大的信和贺卡,邮政自行车根本装不下,都是专门开面包车一样大的邮车来接的。”现在已经看不到王霞回忆中邮筒塞得满满当当,仓门一开,信就滑出来甚至有的信都摆在邮筒外面的场景了。“那时候还很流行音乐贺卡,从邮筒送到邮局后需要过戳。现在信少了都是手工盖邮戳,以前都是过戳机。过戳机一压,有的音乐贺卡就坏了,咿咿呀呀一直唱着,邮递员也不会专门把它找出来,就让它一直唱歌,还没到目的地它就唱哑了喉咙。”
邮局在王霞小时候的印象里只是一间小小的店面,后来慢慢发展壮大。“以前邮局还会给员工分房子呢,上海一间房什么概念,有钱吧?”1998年,邮政和电信分家,电信一天天壮大,邮局也一点点失去往日的辉煌。关于邮局的没落,王霞觉得部分原因是网络与手机的普及。她怀念过去写信的时光,总觉得手机聊天少了点味道,“现在的人哪能理解从前信上几个字里的思念。”
信件一封封地少了,这个地界上开筒的邮递员也渐渐从三个变两个、从两个变成现在只有王霞一人。随之而来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对邮递员工作的轻视与不屑,王霞对此很不理解。“我没觉得体力活有什么不好的。学习的苦你吃不了,你就要吃身体的苦。更何况我喜欢运动带来的自由和愉悦。确实累,但我做完一天的工作就一下子轻松了。”
她最近听说因为信件越来越少,邮局要重新划分地界了。“收紧”是王霞形容的邮局现状,但她并不是十分在意,“反正我还有三年就退休了,接着干下去呗。”

王霞开邮筒时骑的邮政电动车
劳模与“小市民”
“我没什么好采访的,你要想写东西我可以帮你联系我们邮局的劳模,媒体报道过的。”一开始面对采访,王霞如是说道,显得有些局促与惊讶,“我们的工作很普通,没什么好写的。”
王霞所说的劳模是与她一同隶属于普陀区曹杨新村邮政支局的邮递员叶其懂,与王霞不同的是他曾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感动上海年度十大人物以及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她还提到另一个邮局劳模——走川藏线的邮车司机其美多吉,2011年他曾在运输途中被歹徒砍了17刀。有很多邮递员让她钦佩,他们常年在在深山老林里送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真的是跋山涉水,骑着马,带着信,拴上铁链子吊着铁索过河。还有的地方连马都没有,就是靠背。“太厉害了。”王霞有些自愧不如,“我就是小市民。”王霞一边说,一边弯下腰捡起别人掉在地上的塑料玩具,“但工作上我不会马虎的,哪怕不挣钱,我工作也不会‘捣糨糊’。”
路边的每一个邮筒上都贴着一张精确到分的开筒时刻表,而王霞每天就是按照这个表准时开筒,风雨无阻。王霞对紫外线有点过敏,太阳晒多了就会皮肤红肿,“是自己的问题就要克服”,所以每到夏天王霞就要用帽子、眼镜和口罩把自己整张脸包起来,同事问她为什么不让自己好看点,“那哪能啊!”王霞笑道。
王霞在开箱班做了三年,在普陀区62局地界上,她已经熟记了23个邮筒的开筒时间,从这一个邮筒到下一个邮筒需要多久的时间,王霞能掌握得八九不离十。哪怕她知道哪些信筒哪些时段多半会是空的,“还是要去开的,其实就是工作的责任心。”

王霞正准备打开邮筒
做投递员的16年里,王霞也遇到过不少麻烦,有一次甚至被扇了耳光。“那户人家搭棚子占据了整条马路,她不同意把棚布撩起来让我过去,于是吵起来了。后来警察来了,那户人家也道歉了,我心里还是不甘,但无论怎样第二天我还是得去他们家送。” 投递员是有专门的服务操作规范,客户有要求时需要入户投递。几次王霞负责早上投递时,会遇到刚睡醒穿着底裤就来取件的人,“很尴尬,”王霞微微摇了摇头,“但是再尴尬也必须要干。”职业道德,是王霞在聊天过程中反复挂在嘴边的。
“我就是阿Q精神”
王霞与她母亲一起住在梅岭北路上的老小区,到她工作的邮局走路只要六七分钟。
推开两道保险门,王霞一进屋就喊了声“妈”,换上拖鞋后把中国邮政的外套挂在了椅背上。王霞母亲从没开灯的房间里走了出来,问了句今天吃什么。王霞今天没有去买菜,说了声都行。
“榨菜蛋汤可以不?”
“可以的,行!”
聊起母亲,王霞少见地皱起了眉,“她不让我做饭,看见我衣服放着就一定要帮我洗。但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也不想让她那么辛苦了,她这样对我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王霞连着重复了三遍“我妈对我太好了”。
王霞的家有五十几平米,平时只有她和她母亲住在这儿。虽然面积小但干净整洁。在王霞的房间,床上除了床品外还摆放着一套她的睡衣,电视柜上没有电视。她特地买了一个石头做的壁虎雕塑,套上浅青色的大发圈,来遮挡装修时为装电视而预留的洞。只有床头的柜子是她的小天地。最上面一层摆着二十余本书,第二层是她喜欢的一些香水和香料,有盘香也有祖玛珑,桌面上摊开着一本名叫《益寿文稿》的杂志,是邮局多出来的。那一页上还留着王霞的笔记,“我觉得思考了就是一种积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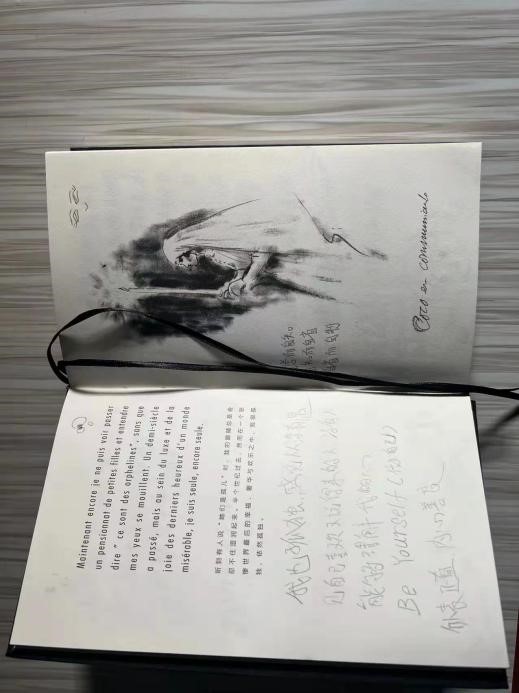
王霞读书时留下的笔记
吃完饭王霞就回到她的房间,换上睡衣,一个人玩着手机。她的社交很少,比起吵闹的事情,她说自己更喜欢一个人静下来做自己的事,所以她也很少与同事聚餐。“很多人不理解我,但我觉得自己愉快就好,我不管别人。”她也没有子女,当王霞知道自己生的孩子可能会患溶血病时就放弃了生孩子的想法。“遗憾其实是有的,但并没有那么的遗憾。但生下来就得负责,不能让我的孩子痛苦。”问及会不会感到孤独,王霞还是坦率地点了头。
“我们家在家族里可能是最穷的,我们的亲戚都是律师、商人、老师、校长、博士、医生、邮局局长,他们的孩子很多都是送到国外读书,有的亲戚有钱到逛个街就能买个房。”王霞拿起手机,滑动着列表,点进亲戚们的朋友圈,安静地看着他们的生活。王霞母亲说她不跟亲戚交往,上不了台面。
“我自卑,我跟他们不是一类人。我只是个普通的邮递员,根本不能比。”
王霞压着嗓子说话,停顿了几秒后又主动打破了这凝固的尴尬。“我住在老小区,住在‘穷窝’里,就是想给自己一种自信,觉得自己也还可以。其实就是阿Q精神。”
王霞经常说话把同事逗乐,因此大家都喊她“逗逗姐”。王霞称自己是无奈的乐观,“你牢骚埋怨都是伤害自己。本来生活就有压力了,你就别去想,专注做好眼前的事,让自己开心点。”
采写 | 20级新闻学双学位 沈杰怡

